網路與書16《記憶有一座宮殿》
(New Palace of Memory)
![]()
 記憶之宮
記憶之宮
文─郝明義 圖像創作-滿腦袋
4.
西塞羅所以在《論雄辯》
這本書裡,談西末泥德以及他所發明的記憶術,是因為他把「記憶」(memory)視為辯論術中五大重點之一。
希臘、羅馬的文化中,藝術與建築的發展,都極為璀璨。在那麼多豐富而精彩的雕像、建築的環繞中,他們會在辯論術中利用到結合「空間」與「心像」的記憶法,是十分自然的發展。
一個要發表一篇滔滔雄辯的人,當然是不能帶小抄的。這樣,如果他能把一篇演說的內容,事先儲存在腦海裡架構出來的宮殿之內,則他在演說的時候只要讓自己進入要遊覽那座宮殿的狀態,那麼只要他把宮殿裡最精彩的空間裡的陳設瀏覽過一遍,他精彩的演說也就無所遺漏了。
利瑪竇說,這樣的記憶之宮到底要建築多大,端視需要而定:「用多,則廣宇千百間;少,則一室可分方隅」。進門之後的行進路線,則「爰自入門為始,循右而行,如臨書然。通前達後,魚貫鱗次,羅列胸中」,一方面提出了一種遊覽路線的可能,一方面還告訴我們這些腦海中的遊覽之順暢,根本可以像揮毫寫一幅字般輕鬆自如。
5. 法蘭西絲.葉茲(Francis Yates)
的《記憶的藝術》(The Art of Memory),是一本不能不讀的書。這本書把西方這種心像記憶法的傳承,做了極其生動又詳盡的描述。
從這本書的整理,我們可以看到西末泥德的方法,如何經亞里士多德而至羅馬時代。羅馬時代除了西塞羅之外,如何又有昆提連(Quintilian)一派,及佚名所著《獻給海倫留姆》(Ad Herennium)的一派之發展。
基督信仰成為主流之後,希臘、羅馬時代的種種文化成為異端,遭到破壞。但是心像記憶法卻並沒有失傳,反而更形發揚光大。只是其中羅馬的宮殿與神祇雕像,被《聖經》裡的空間與心像所取代。其理論的發展,歷經奧古斯汀而至阿奎那到達一個高峰;其實際的使用,則以但丁的《神曲》中天堂與地獄的刻劃到達一個高峰。
在天主教「謹慎」 (Prudence)、忍耐(Temperance)、正義(Justice)、毅力(Fortitude)的基督四德中,「記憶」成為「謹慎」重要的一環。耶穌會神父利瑪竇會如此嫻熟使用心像記憶法,其來有自。
6. 1455年,古騰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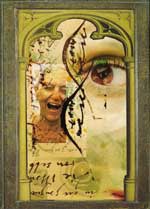 在西方發明了活版印刷術。書籍開始可以快速、方便、成本低廉地印製,結束了手抄本書籍的時代,打破了知識長期被封鎖在中世紀神職人員的侷限,也為心像記憶法的必要寫下了一個問號。
在西方發明了活版印刷術。書籍開始可以快速、方便、成本低廉地印製,結束了手抄本書籍的時代,打破了知識長期被封鎖在中世紀神職人員的侷限,也為心像記憶法的必要寫下了一個問號。
文藝復興之後,人文思想大盛,心像記憶法因為與神學的結合太深,自然開始受到質疑。
布魯諾(Giordano Bruno),在心像記憶術的發展上,是個具有特別意義的人。一方面,出身於修道院的他,後來結合占星術與種種新奇知識的研究,為心像記憶法做了歷史性的總結與大成;另一方面,他也因為反對以神學為一切的思想,支持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而終於被教會審判八年之後,燒死於羅馬的教會廣場。他個人所象徵的二千多年心像記憶術,到了顛峰,也預告了沒落。
接於布魯諾死後而起的啟蒙時代,為心像記憶法的問號改劃下句號。這有許多理由。其一,如法蘭西絲.葉茲所說,萊布尼茲發明微積分之後,給想像的世界提出新的抽象符號,並做出無限的延伸。第二,各種新生知識開始出現系統化的整理與發展,人類學習與記憶的對象,轉向分門別類的知識領域。第三,這也和工業革命之後,新生的學校制度有關。
心像記憶術,從來都不是一個有定法可循的學習之道。教導心像記憶法的人,都是給一些原則,然後舉幾個例子來說明。至於實際最重要的如何建構那些記憶之宮,記憶之宮裡的陳設究竟如何,並不多加指導。這是因為心像記憶法強調每個人的記憶之宮都應該由他自己來建構,所以如果拿他人太詳細的例子來當範本,反而有違原則,不利自己記憶之宮的發展。
當工業革命之後,現代化大量招生的學校出現,講究標準教材來教學,教學重點在科學的教育制度大興。相較之下,心像記憶法是在知識屬於少數人擁有的時代個別傳授的方法,是意會重於言傳的方法,再加上與科學相對立的神祕與宗教色彩,被時代所「淘汰」也就毫不足為奇了。
如果說過去的心像記憶法是在教人如何建造記憶中的宮殿,所需要的是個人而隨機的藝術與想像,那麼在工業革命之後新興的學校制度之下,我們開始學習的則是如何建造記憶中的倉庫──在倉庫中,如何有效率地整理與存取大量、規格化、標準化的知識。
從宮殿而倉庫,不論在我們的腦外還是腦中,都是近代的一個進程。(本文節錄自網路與書《記憶有一座宮殿》<記憶之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