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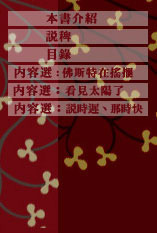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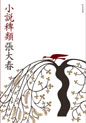 |
||
| 作者:張大春 定價:350元 ISBN:957-29567-6-0 初版日期:93年11月 |
||

佛斯特在搖擺 ─ 一則小說的因果律 距今整七十年前,佛斯特(E. M. Foster, 1879-1970)在母校劍橋大學發表了《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系列專題演講,結集成書之後,影響─或者毋寧說:予人之印象;深遠。現在是一九九七年的春天,你站在任何一所未必然是劍橋的大學文學院裡,攔住一位野心勃勃、想搞小說理論的年輕人,向他請教本行的必備經典,倘若他沒提這本《小說面面觀》,也許是因為他覺得這本書的觀念、理論都過時了,要不,就是以跟上流行論述舞步為務的學院澈底忘了佛斯特的理論。 一九二七年,肉體和創作生命正走在高峰之上的佛斯特一定能夠預先察覺到這種即將被忽視或遺忘的命運,至少在《小說面面觀》的結語裡,他謙遜地表示:他(以及任何有能力或地位的小說家)並沒有權力「對小說的未來作某些估量」,因為「我們曾經不讓過去做我們的絆腳石,就不能以未來作獲利的工具。」 這樣的謙遜恐怕祇及於對「未來」比較容忍而已。佛斯特的理論從來沒有真正優惠於值得同情或親切理解的經典─比方說:亞理斯多德的《詩學》。《小說面面觀》必欲除《詩學》而後快的急切感果然是躍乎紙面的;否則佛斯特不至於在論情節的第五章中這樣寫道:「亞理斯多德實在可以隱退了,至少,從小說的領域中退出,並且把他那些有關情節的論調一併帶走。」 佛斯特儘可以佔盡時間所賦予的便宜而去調侃亞理斯多德「讀到的小說不多」、「當然沒有見過現代小說」、「所謂內在活動根本不合他的胃口」,但是,佛斯特對小說的情節又有多麼超越時空的見解呢? 突然來了一個定義 「我們得對情節下個定義。」佛斯特這樣說道:「我們對故事下的定義是按時間順序安排的事件的敘述。情節也是事件的敘述,但重點在因果關係(Causality)上。『國王死了,然後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則是情節。」 在「國王與王后」這樣通俗易懂的例證下,佛斯特並沒有「超越」亞里斯多德的發現;而亞里斯多德也並不須要讀「夠多的小說」才能提出「情節的根本特徵是因果關係」,他早就說過:「在完好的情節之中,每一事件不是有前因,就是有後果。」當他指稱情節為「行為的摹仿」的時候,也從未因胃口問題而摒除過人類的「內在活動」。佛斯特在劍橋講堂上可能不認為在座的學生當真對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有什麼親切的體會,否則,一方面高喊著讓亞里斯多德隱退,一方面卻又悄悄拾起《詩學》的甲冑作為自己立論的武裝,著實放肆又大膽。這突然冒出來的一句「我們得對情節下個定義」似乎也祇能讓原本不懂小說藝術的讀者(其中也可能不乏作者和批評者)以為他「更懂」了一點,道理很簡單:「國王與王后」的例子實在太好懂了。但是,「『國王死了,然後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則是情節。」恐怕祇能簡化我們對情節這個課題的理解,它與絲毫無助於我們對「因果律為什麼會是情節的根本特徵?」這個問題的深刻認識。 國王死了,王后在花園裡散步 直截了當地回答「因果律為什麼會是情節的根本特徵?」將使問題顯得有些玄遠,因為因果律是人類對時間之流中發生的諸多事件所能採取的最方便的解釋方法。無論是一齣戲劇或一部小說,既不能包羅萬有地展現人生散漫又瑣碎的全貌,又不得不讓它的觀眾或讀者感知它是一種「人生的摹仿」,而它又始終不能「說明」它為什麼沒能把任何一個角色的人生(像哈姆雷特或艾瑪•包法利或賈寶玉)展現得更為完整(哪怕是他們一生中某一天的、巨細靡遺的日常細節和心理活動)。正由於「完整展現」之不可能,作為「人生的摹仿」的敘事藝術便不得不放棄它與時間作等速再現的角力,轉而改變對「完整」這個概念的要求。 被切割過、挑選過、篩濾過的「人生的摹仿」怎麼可能「完整」呢?亞里斯多德給了我們一個近乎語言遊戲的答案;他表示:在戲劇裡,祇要所摹仿的行為有一個開頭、有一個中腰、有一個結尾,它就構成了整體。所謂開頭,就是「沒有事物發生於其前,而必有事物自然地發生於其後。」所謂中腰,就是「跟隨於某事之後,同時又在另一事之前。」所謂結尾,就是「必有事物發生於其前,而必無事物發生於其後。」 看似首尾連腰一應俱全的圖式類比包庇了亞里斯多德的完整論─一則改變了對「完整」這個概念的要求,使作品看似「完整」的謊言於是誕生。從公元前三百三十五年左右,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裡關於情節的規範就像日後佛斯特的「國王與王后」一樣,便宜行事地提供了敘事藝術的美學方針。然而,有哪一部作品的內容果真可以被切豬肉一般手起刀落地割成頭、腰、尾三部位呢?有哪一塊被切出來的部位又的確在皮毛骨肉各方面都不屬於另一部位呢?真正值得疑慮的問題還在後面:為了顯示作品本身之「完整」而規範出來的因果律憑什麼成為情節的根本特徵呢?如果「國王死了」,「然後王后在花園裡散步」,可不可以不被解釋成「王后因為思念國王而在花園裡散步」?可不可以不被解釋成「王后因為感受到解脫而在花園裡散步」?可不可以不被解釋成……王后祇是在花園裡散步,可不可以? |
| n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