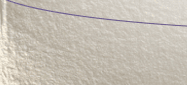我在巴黎的孤獨生活
我進了巴黎,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就走的這條路;我住進同一家旅館,在槌球場路:我只知道這一家。我睡在上一次住的那個房間的旁邊,但是這套房稍大一些,而且臨街。
我的哥哥,或是對我的舉止感到為難,或是憐憫我的靦腆,根本不帶我出去,不介紹我認識任何人。他住在蒙馬特區的壕溝街;我每天三點鐘去他那裡吃午飯;然後我們分手,第二天才再見面。我那胖表兄莫羅已不在巴黎。我有兩三次從德‧夏斯特奈夫人的府邸前經過,但是不敢向門房詢問她的近況。
秋天開始了。我六點鐘起床,去騎馬場,然後吃早飯。幸虧那時我酷喜希臘文:我翻譯《奧德賽》和《遠征記》(1),直到兩點鐘,中間穿插著研究歷史。兩點鐘,我穿好衣服,去我哥哥那裡;他問我做了些什麼,看見了什麼;我就回答說:「沒做什麼,沒見什麼。」他聳聳肩,轉過背去。
有一天,我們聽見外面有響動;我哥哥跑向窗口,招呼我也過去,但我那時正坐在房間後面的扶手椅上,不想站起來。我可憐的哥哥於是預言說,我將來一定會默默無名,無疾而終。
四點的時候,我回旅館;坐回我的窗扇後面。兩個十五、六歲的少年這段時間會到馬路對面一家旅館的窗邊畫畫。我發現了他們活動的規律,他們也發現了我活動的規律。漸漸地,他們抬起頭看看他們的鄰居;我非常感激這種關切的表示:他們是我在巴黎的唯一的交往。
晚上,我去看戲;觀眾冷落,這使我很高興,儘管我得多花點兒錢到門口買票,跟別人擠在一起。我修正了我在聖馬洛時對戲劇的觀念。我看見了聖-於貝爾蒂夫人扮演阿爾米德
(2);我感覺到了我創造的那個女魔術師缺了點兒什麼。當我不把自己關在歌劇院或法國人劇院的大廳裡的時候,我就在大街小巷或沿濱河路漫步,直到晚上十點、十一點。今天,我仍然一看見從路易十五廣場到善人門那一長列路燈,就想起我順著這條路前往凡爾賽覲見時所感到的恐慌。
回到住處,我低頭朝著爐火,待上一段時間,那爐火什麼也不對我說:我不像波斯人那樣有足夠的想像力,把火苗當成銀蓮花,把火炭當成石榴。我傾聽著車輛來的來,往的往,交錯而過,其遠遠的隆隆聲很像大海在我的布列塔尼的沙灘上低語,或者風在我的貢堡樹林中淺吟。世界的這些聲響讓人想到孤獨的聲響,喚醒了我的悔恨;我想起往日的痛苦,或者,我的想像編織出這些車輛帶走的人們的故事:我隱約看見輝煌的客廳、舞會、愛情、征服。很快,我便醒了,又發現自己被遺棄在旅館裡,從窗口望著世界,在內心的回聲中聽著世界。
盧梭認為由於他的真誠,或者為了教育人,他才懺悔他一生中那些可疑的快樂;他甚至以為別人是鄭重其事地詢問他,要求他坦白他和威尼斯的那些危險女人
(3) 所犯下的罪孽。假如我混跡於巴黎的娼妓堆裡,我不認為我必須以此教育後人;然而,我一方面太靦腆,一方面又太狂熱,不可能讓妓女們誘惑了去。她們勾搭行人,拉他們爬上她們的夾層,就像聖克魯的馬車夫拉人上他們的馬車一樣,我走過這些不幸的女人群時,感到厭惡和害怕。只有逝去的時代的冒險樂趣才適合我。
在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世紀,不完善的文明,迷信,奇特和半野蠻的風俗,在故事裡隨處可見:性格是強悍的,想像是有力的,生活是神祕而隱蔽的。夜裡,在公墓和修道院的高牆周圍,在城市的冷冷清清的圍牆下,沿著集市的鎖鍊和壕溝,在封閉的街區的邊緣,在狹窄的、沒有路燈的街上,小偷和殺人犯埋伏著,幽會有時在火把下進行,有時在濃重的黑暗中進行,赴某個愛洛依斯應允的約會是要冒著失去腦袋的危險的。為了放蕩一下,得真愛才行;為了違反一般的風俗,必須做出巨大的犧牲。問題不僅僅在於面對意外的危險和藐視法律的利劍,人們還必須在自身上戰勝日常習慣的控制,家庭的權威、地方的風俗、良心的衝突、基督徒的恐懼和責任。所有這些障礙都加強了激情的力量。
我不會在一七八八年跟著一個可憐的飢餓的女人在警察的監視下進入她的破屋;然而我可能會去追求一六0六年巴松彼埃爾 (4) 敘述得如此精彩的那種冒險。
「五個月或六個月前,」元帥寫道,「每次我走過小橋(因為那時新橋還沒有建),總有一個美麗的女人,掛著『兩天使』招牌的洗衣女,對我行深深敬禮,緊盯著我直到看不見為止;由於我警惕她的行動,就也看著她,更關心地向她致意。
「有一回,我從楓丹白露回到巴黎,經過小橋,她一看見我,就站在她的鋪子的門口,在我經過時對我說:『先生,我是您的奴僕。』我還禮,不時地回頭,我看見她的目光一直跟著我。」
巴松彼埃爾得到一次約會:「我看見一位很漂亮的女人,二十多歲,著晚妝,身穿細薄的襯衫,綠色的小裙子,腳上是高跟拖鞋,身上披著浴衣。我非常喜歡她。我問能否再見到她。她說:『如果您想再見到我,那就是在我的一個嬸嬸那裡了,她住在神甫鎮街,在菜市場附近,挨著熊街,從聖馬丹街那頭數第三個門;我在十點到午夜之間等您;再晚些也行;我讓門開著。門口有一條小過道,您得趕快過去,因為我嬸嬸的房間的門正對著,您會發現一個台階,通到三樓。』我十點到了,找到她指給我的那個門,燈很亮,不但是三樓,四樓和一樓都很亮;但是門關著。我敲門告訴我來了;可是我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問我是誰。我回到熊街,第二次又去,發現門開了,我進去,直上到三樓,發現那亮光原來是有人點著了鋪草,兩具裸露的軀體躺在房間裡的桌子上。於是我退出了,驚駭莫名,出門的時候,我碰見了幾個烏鴉(埋死人的人),他們問我找什麼;我推開他們,拔出劍來,不理會他們就衝了出去,回到我的住處,這意料之外的景象使我頗不舒服。」
我根據那個地址,也去尋找二百四十年前巴松彼埃爾的發現。我過了小橋,穿過菜市場,沿聖德尼街直到熊街,上了右手一側;左手第一條街通到熊街,正是神甫鎮街。街牌被時間和火災燻黑了,我感到很有希望。我找到了從聖馬丹街那頭數來「第三個小門」,歷史家的材料真可靠。不幸的是,我開始還以為仍然存在於街上的兩個半世紀已經消失。房屋的門面已是現代的了;二樓,三樓,四樓,都沒有任何光亮。屋簷下,頂樓的窗戶上雕滿旱金蓮和香豌豆花飾;底層有一家理髮鋪,玻璃後面掛著好幾種樣式的頭髮。
我非常失望,就進入這座艾波尼娜 (5) 博物館:自從被羅馬人征服以後,高盧女人就一直把她們金色的頭髮賣給那些頭髮不那麼漂亮的人;我的布列塔尼的女同胞在某些有集市的日子裡仍然把頭髮剪下來,用她們的自然的頭巾換一方印度紗巾。我問一位理髮師,他正用一把鐵梳子梳理一頂假髮:「先生,您曾經買過一個年輕的洗衣女的頭髮嗎?她住在掛『兩天使』招牌的那個地方,在小橋附近。」他一下楞住,既不能說是,也不能說否。我百般道歉,穿過一綹綹頭髮的迷宮,出去了。
隨後,我一個門一個門地找:根本沒有什麼二十歲的洗衣女向我「深深敬禮」;根本沒有什麼直率、無私、熱情的年輕女人,「著晚妝,身穿細薄的襯衫,綠色的小裙子,腳上是高跟拖鞋,身披一件浴衣」。只碰到一個囉嗦的老太婆,馬上就要到墳墓裡去找她的牙了,想用她的拐杖打我:這大概是那次約會裡的嬸嬸吧。
巴松彼埃爾的這個故事是一個多麼美的故事啊!讓人理解他被愛得那麼堅決是有理由的。那個時代,法國人還被分作兩個界限分明的階級,一個是統治階級,一個是半農奴。洗衣女擁抱巴松彼埃爾,就像一位半神落進一個女奴的懷裡:他給她一種勝利的幻覺,而女人中的法國人是能夠陶醉於這種幻覺的。
然而,誰能告訴我們那場災難的不為人知的原因呢?是那個「兩天使」的可愛的小女工嗎,她的屍體和另一具屍體一起橫在桌子上?那具屍體是誰的?她丈夫的,還是巴松彼埃爾聽見聲音的那個人的?是瘟疫(因為那時巴黎有瘟疫)或妒忌在愛情之前來到了神甫鎮街嗎?在這樣的主題上,想像力可以自由馳騁。只需在詩人的創造之中攙進大眾的心靈、來到那裡的掘墓人、遇上巴松彼埃爾的劍的「烏鴉」,一齣絕妙的情節劇就從這次冒險中產生了。
您也會讚賞我年輕時在巴黎的貞潔和節制的:在這座首都,我很容易胡作非為,就像在德廉美修道院 (6) 裡,人人為所欲為;不過,我並未濫用我的獨立:我只跟一個二百一十六歲的妓女來往過,她曾被一位法國元帥愛上,而這位元帥是那位貝亞恩人
(7) 為了德‧蒙莫朗西小姐的情敵,是德‧昂特拉格小姐的情夫,而這位小姐是德‧維爾那依侯爵夫人的姐妹,後者說了亨利四世那麼多壞話。我將要去覲見的路易十六,他一定想不到我和他的家族還有過這種祕密的關係。
一八二一年三月,柏林。
1 古希臘歷史家色諾芬的作品。 (回到段落)
2 十七世紀一齣著名歌劇的女主人公,是一個愛上一位法國軍官的女魔術師。 (回到段落)
3 原文為義大利文。 (回到段落)
4 法國元帥(1579-1646)。 (回到段落)
5 高盧女英雄,死於公元79年。 (回到段落)
6 典出拉伯雷《巨人傳》。
7 指亨利四世。
‧試讀‧我在巴黎的孤獨生活‧橫越大西洋‧概述我這一生中地球上的變化 ‧
|